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环境问题:
2009年12月30日,上海,位于茂名北路的蕃祉里,拆迁废墟下压着几个服装“模特”。
在北京待了20年,徐福生因为拆迁需要已经搬了十几次家,“从四环被撵到了五环,又马上要被撵去六环了。”
不过每次“被搬家”,徐福生都很高兴。这位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生意人表示:“还要拆,就还有生意做。”
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分三六九等:施工现场废弃的破旧门窗、泡沫板、铜铝铁都是好东西;渣土、碎砖石则是真正的垃圾,“连我们捡破烂的都不要,还有谁要”?
答案是土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博士高世扬花了近1年,调查北京建筑垃圾的回收情况。他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北京每年产生4000万吨建筑垃圾中,回收利用的还不到40%,其余都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一数字远高于北京每年7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为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焦头烂额时,建筑垃圾正如一头无人约束的猛兽,悄悄地吞噬我们的城市。
“无人约束。”高世扬再三强调说。据他调查,只有10%的建筑垃圾会被运往指定的消纳场所,其余的或被随意倾倒,或被运往非法运营的填埋地进行处理。
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2003年,徐福生发现建筑废品的产生量和需求量同时大增,将事业重点从生活垃圾转向了建筑垃圾。
后来,他听说那一年正是围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城市建设启动年。从那一年开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从3000万吨激增至4000万吨,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一年的数量。
对此,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欣葵教授解释说,城市化的大跃进是建筑垃圾产生的主要动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筑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刘欣葵告诉记者,“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以这么高的建筑垃圾产出量作为发展代价?”
在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崔素萍撰写的《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现状与资源化》的报告中,记者发现,因老旧城区拆迁和市政工程动迁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装潢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20%。
根据行业标准,不同的来源直接关系到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以每万平方米计算,施工这么大面积的房屋将产生500吨~600吨垃圾,如果拆除同样面积的旧建筑,垃圾产生量就将多了13倍,高达7000吨~1.2万吨。
刘欣葵指出,很多老旧城区的建筑并未到达50年的标准使用寿命,可以通过内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换。“在技术上100%可以做到,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刘欣葵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立军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研究团队用了1年为一条历史街区设计改造方案,可以“不伤一兵一卒”地将住宅区转化为商业区。最终,方案在开发商的手里夭折,历史街区变成了百货大楼。
“只剩下一面花了几百万保留下的古墙,他们说这代表了对街区的保护。”周立军回忆,“其他的都没有留下,其实,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无人问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扬略带愤怒地展示他拍摄到的照片,被随意倾倒的碎砖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刚刚遭遇了地震袭击的城市。
在一次实地勘探的过程中,高世扬就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打算拍摄地震中救人的场面,就把拍摄地点选在了垃圾场。
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计算,北京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1850万吨,1999年的台湾地区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2000万吨,唯一“无法比拟”的是产生了1.7亿吨建筑垃圾的汶川特大地震。
“再加上广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扬开了个小玩笑,但随即绷紧了面孔,“其实,它们都是灾难。”
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
偷运建筑垃圾是秦伟的工作。
白天,他和工地的工头们谈好价格,“看运距远近,一车200元,熟人便宜20元。”一入夜,那辆他花4万元买的二手卡车就要奔驰在五环路上,往返于工地和填埋场之间。所谓的填埋场都是当地村民承包的,消纳程序很简单,“倒进坑里就得了”。顺利的话,秦伟一夜能倒3车。
“万一被城管逮到了,一个月的收入就泡汤了。不过别的地方都还好,就东五环的城管查得严点。还好他们就要钱,不要那些东西。”秦伟透露。
早在2004年,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通告》。通知要求建筑垃圾的产生单位,要到工地所在区的渣土管理部门办理渣土消纳手续,并申报车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路线把渣土运输到指定的消纳场,然后进行填埋等处理。
但在调查中,高世扬发现,北京市垃圾渣土管理处渣土办公室只有5名工作人员,“这是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啊,怎么打得赢”。
一个包工头曾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陈家珑教援透露过行业的潜规则。由于承载力有限,北京市指定的20多家正规消纳场也不愿意消纳建筑垃圾,由于“上面规定大工地一定要与指定消纳场签署合同”,所以双方在底下达成了默契,“合同照签,但是消纳场只收很少的消纳费,交换条件就是工地自行消纳”。
一条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纳链就此形成。陈家珑很保守地估计,大约90%以上的建筑垃圾都没有通过正规渠道消纳。连秦伟都觉得垃圾真不少。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坑都要排号等着”,甚至那些填埋场都不再填埋,而是雇车将这些建筑垃圾运到更远的地方。
“这些建筑垃圾,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曾经主持过“首都环境建设规划项目”的刘欣葵表达了她的担心。
由于缺乏有效分类,建筑垃圾中的建筑用胶、涂料和油漆不仅难以降解,还含有有害的重金属元素,长埋底下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地表沉降。
而最大的风险在于其占用了大量土地。根据陈家珑的计算,每万吨建筑废物占地2.5亩。未来20年,中国的建筑垃圾增长会进入高峰期,将直接加剧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冲突。
“城市化是一个外扩的过程,有朝一日,当我们需要在被建筑垃圾填埋的土地上进行建设的时候,建筑成本将大大提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总工程师刘航认为。如果缺乏规划,被填埋的建筑垃圾根本无法作为地基使用,还要面临建筑垃圾再转移的问题。
三千里锦绣江山就要变成垃圾江山
当徐福生还在琢磨回收建筑垃圾是否赚钱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开始进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的研发了。根据现有技术,95%以上的建筑垃圾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循环利用。
2003年,做沙石生意起家的吴建民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建成了北京市首家建筑垃圾处理厂,并建成了年消化100万吨建筑垃圾的生产线。
让吴建民措手不及的是,原料来源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厂子建在六环外,很少有运输车愿意承担过高的运费,而更习惯将建筑垃圾就近填埋。如果自主承担运费,赔得就更多了。
7年来,吴建民已亏损上千万元,工厂也已经停产。如今,唯一能让他感到“未来还有希望”的事情,就是新闻联播“还在宣传循环经济”。
据说,全国类似的建筑垃圾处理企业还有20多家,大部分都面临困境。相比于韩国、日本90%以上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我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还不到5%。
另一组数据是,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约为3亿吨,而50年到100年后,这一数字将增至26亿吨。
令陈家珑难忘的是,当得知韩国推行《建设废弃物再生促进法》的消息时,一位专家和他开玩笑:“再不强制推行建筑垃圾资源化,这三千里锦绣江山,就要变成三千里垃圾江山了。”
刘欣葵教授则告诉记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建筑垃圾的产生成本并没有很好地纳入城市运行成本的计算。“建房是住建委的事儿,而建筑垃圾却是市政市容委的事儿”,“连分管的市长都不一样了。”
“其实,正确的路,我们走过,只是忘记了。”在调研过程中,高世扬发现,在1978年以前,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拆除下的城砖由规划局分配,首先要拨给有建设需要的单位进行再利用。
那时候,它们被称为拆除旧料,而不是建筑垃圾。高世扬坚持认为,是1988年土地市场的成立,让建筑垃圾变成了市政市容问题,土地开发则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心。
“建筑垃圾就是钱的问题!”徐福生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能生钱的就要重视,不能生钱的,当然没人管了。”
还有两个月,徐福生又要搬家了。他现在住的地方被划入了“50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范围。这也意味着,他生意的旺季又要来了。只是这次,徐福生有点喜忧参半。
“再撵就有点远了,废品的运费又该提高了。”
作者:林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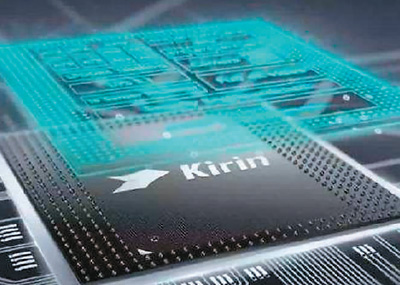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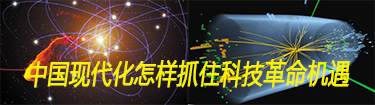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