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怕什么?
别怪我想的时间长。毛泽东英雄一世,论及一个“怕”,谈何容易?你又加个“最”字,毛泽东是讨厌“最”的,他说一“最”就脱离群众,变成孤家寡人了。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有三怕。
一怕泪。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就怕听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确实如此。
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我们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
渐渐接近了,我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看清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我的手离开了枪,这孤儿寡母的绝不会构成威胁。我的责任只是保卫主席安全,其他事情不去多想。我甚至轻松地吁了口气。
可是,在我松气之际,毛泽东却身体一阵震颤,叫道:“停车!”
司机周西林把车煞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过去都是我们卫士去开门扶他下车。毛泽东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我在这里。”朱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的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屋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那时,抗生素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 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二怕血。
二怕血。
你会说:“瞎扯!毛泽东身经百战,指挥战役大大小小何止千百次?战场上哪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毛泽东的亲人和朋友牺牲有多少?那长长的名单证明毛泽东从未在敌人的凶残面前有丝毫恐惧和退缩。
可是你别忘了,我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
进城后,毛泽东开始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在山上的还有不少中央首长,其中不乏儒将武将。这些将军们听惯了枪炮声,都是子弹堆儿里钻出来的人,一下子没仗打了,耳边只剩下鸳歌燕舞,那是很不习惯,很不适应的。何况还有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个个都是操枪射杀的惯手,几天不打枪真是手痒心痒全身痒。
不知是谁挑头开了第一枪,于是大家都找到了解痒的法子。香山有的是乌雀,打吧!噼噼啪啪的枪声便打破了香山的宁静。说实话,那时还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世界上也没有那个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解放战争还在南方猛烈进行,死几干人都不算啥,何况打几只鸟?
那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我随他回到双清别墅。才下车,正有几名警卫干部打 了麻雀回来。他们枪法好,打了很多,拴成一串,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毛泽东听到欢笑声,朝那边望了一眼,只是随便望了一眼,突然停住了脚。那几名警卫干部见到毛泽东,礼貌地停止喧哗,放慢脚步。
毛泽东眉梢抖动一下,渐渐皱拢,习惯地吮吮下唇,问:“你们拿的什么?”
“打了几只家雀。“一个同志将那串麻雀举向毛泽东。我清清楚楚看到了沾满鸟羽的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
毛泽东面孔一抽,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退了半步,突然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
那同志吓得赶紧将滴血的麻雀藏到身后。
“谁叫你们打的?”毛泽东皱紧眉毛责问:“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
几名同志无言以对。
“以后不许打,任何人不许打!”
“是首长们先打的。”我悄悄解释,“后来大家才跟着打……”
“今后任何人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不许打!”
此后,那些疲于奔命的鸟雀又有了安定宁静的生活环境,得以自由歌唱翱翔,屋热热闹闹地繁衍子孙。
后来,又有专家说,麻雀也吃毛毛虫,功过各半。于是,全国才停止了那场为丛驱雀的运动。
还有件事给人印象深。
大约是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春藕斋参加跳舞活动。休息时,他坐在沙发里吸烟。一名参加舞会的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走过来,坐到毛泽东身边,同毛泽东聊天。谈到文工团员的学习训练时,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练功累不累?”
“累,挺苦的。”女团员眨眨眼,又说:“有时还会出事故呢。”
“还会出事故?”毛泽东惊讶不解。
“可不是吗,听说天津一家剧团里,演《哮天犬》的演员练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一直戳进……”
“哎呀,”毛泽东脸孔抽缩着露出惨不忍睹的样子,头扭向一边,连连摆手:“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他喘息一口,定定神,好像要摆脱那悲剧似的,起身匆匆走到一边。
乐曲再起时,他皱着眉头坐在那里,没有下场跳舞。
三怕喊饶命。
三怕喊饶命。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从不曾像寓言中的祖先那样将冻僵的毒蛇暖入心口窝。无论蒋介石或者其他政治军事上的敌人怎样喊饶命,毛泽东的回答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确实怕听人喊饶命。
在陕北时,斗争生活最艰苦的年代,有名警卫战士受不住了逃跑了,警卫战士逃跑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的逃兵,那是知道不少秘密的呀,泄露出去还得了?
警卫部队立即调动人马追捕,终于将那名逃兵捉住,捆了回来。同志们本来就憎恨逃跑行为,何况为了追逃兵大家受了不少劳累担了不少的心,一肚子的火要发泄便不足为奇了。
“揍那个龟儿子!”
“毙了狗日的!”
愤怒的吵叫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看到押过来的逃兵。那逃兵年纪不大,长了一张娃娃脸,脸色熬白,满是鼻涕眼泪。身上灰土不少,吓得抖个不停。听到喊枪毙,他哇哇地哭叫起来:“饶命,饶命,饶命啊!我不是投敌呀,我是想家啊,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啊!”
毛泽东本是愤恨叛变,憎恶逃跑的,可是,一旦目睹逃兵被抓回来的惨样,他竟悲怜地皱起眉头,眼圈都湿了。他扬起一只手喊:“放了放了,快放了他!”
“他是逃兵! ”
“这小子坏着呢……”
“哪个坏?”毛泽东依然皱紧眉头,“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
一名干部不服气:“这么严重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就带不了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换上温和说服的语气:“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想家,你再关他他不是更想家了?他又不是叛变投敌,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点家,听见没有?”
于是,这名逃兵被放了。不但没受任何处罚,反而连吃几天小灶,当然,这名警卫战士再也不曾逃跑。
我以为,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又是一位多情善感的质朴的常人;他的意志坚硬如钢同他的心地善良柔和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
(本文摘自《卫士长谈毛泽东》作者 权延赤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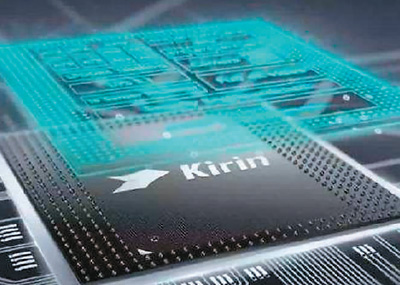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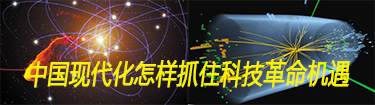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