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导演手记:不为人所知的钱学森
记得是在2006年夏天,美丽的哈尔滨,在中国文献纪录片的一个颁奖仪式上,当时的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薛继军邀我参与《钱学森》一片的拍摄。薛继军是中国纪录片界的资深代表人物,他拍摄的电影《圆明园》为中国电影纪录片的扛鼎之作。他的盛情邀请使我倍感荣幸,居然未加思考就应允了下来。从那时算起,直到《钱学森》出片,前后历五年之久。当时我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供职,其间还先后参与了香港回归十周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六十周年、澳门回归十周年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而《钱学森》的拍摄采访及后期编辑一直在艰难地进行,其中艰辛,不为外人所道。
在中国科学家中,钱学森名气最大。他羁留美国最终归来的早已成为传奇、他主持参与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最重要的高科技成果——“两弹一星”,也成为共和国历史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其重要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科技界的极为崇高的地位。但由于他多年从事高度机密的国防尖端科技工作,他的身影并不在公众视线之下,晚年的钱学森又深居简出,极少参加公众活动,因此钱学森也有相当的神秘性;有关钱学森的文字和影象材料比较稀少,甚至还没有一本的叙述钱学森生平和总结他的科学成就的权威专著。平地起高楼,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拍摄《钱学森》,是我们学习和认识钱学森的人生道路、成就贡献和科学思想,并进而构建钱学森生平描述体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走进钱学森,就像进入一个浩瀚无边的森林,你会有全新的发现和体验,常常处于不断的惊喜当中。以下是我们在采访中的所见、所感和所思,记下几则,以飨观众和读者。
一、我与钱学森的一面之缘
人物传记片《钱学森》摄制组成员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达百人之多,而真正见过钱学森并采访过他的,却仅我一人。
那是1997年,我担任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执行总导演,负责全片一百多位当事人的采访。由于周恩来生前是中共党内与知识分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领导人,加上他一直担任领导“两弹一星”(原子弹、核弹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最高机构——中央专委会的主任,钱学森与周恩来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是《周恩来》一片中的重量级采访人物。我们摄制组负责联络采访对象的统筹告诉我,钱学森办公室说,钱老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要向钱老请示。有一天,钱办打来电话电话,跟我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面谈。纪录片《周恩来》的上百位采访对象中,上至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中央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工人、农民,我们均通过电话或传真联络就能搞定,要求面见汇报,才能决定进行采访的,钱学森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经过层层的哨卡,呈递介绍信、填报会客登记、查验证件,我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一位声音洪亮、面色红润、个头伟岸的军人接待了我。他自我介绍,名叫涂元季,是钱学森的秘书,也是他的学术助手。涂秘书告诉我,钱老退休以后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尤其是电视采访,老人家几年来闭门谢客。但考虑到本片乃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之作,钱老对周恩来有特殊感情,所以老人家破例答应接受采访。
当商量采访具体细节的时候,我提出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屋子,而且要提前一小时为采访布置灯光。涂秘书听后皱起了眉头,他告诉我,钱老家的屋子都非常小,而钱老腿脚不便,无法出门,希望我们不要搞得太复杂,尽量缩短准备时间。我们采访提纲中有关于钱老被美国当局扣押五年,最终回国的一段,涂秘书说,钱老不愿提起这段往事,我们可以采访夫人蒋英。
当时由于我们主要是拍摄周恩来的生平,对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本人并未有更多的研究,涂秘书指出了我们采访大纲中大量的常识错误,其中他谈到,我们所说的“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他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包括原子弹、氢弹在内的核弹和导弹、卫星,称为“两弹一星”,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导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是放在一个一百多米的铁架子上,如果没有导弹,原子弹相当于没有枪的子弹,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攻击武器。人造卫星能否上天,主要取决于其运载工具——火箭,钱学森作为中国的导弹之父,其在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
这次谈话,是我对钱学森了解的第一课,也开启了我对钱学森的兴趣。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国防科工委的宿舍,几排红砖三层家属楼,钱学森的家就坐落在此。一楼是警卫战士的住处,钱老一家住在二楼。进门后,发现这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民居建筑,每个屋子都非常窄小。我们选择了钱老的书房,但由于屋子太小,我们原来准备布置的十个灯,减成了四个,幸亏当天阳光明媚,我们更多地使用了自然光。当我们布置完毕,钱老面带笑容,坐着轮椅被推到了书房。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钱老时年八十有六,由于骨质疏松,基本上已离不开轮椅。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钱学森肤色白皙,脸上并没有很多的皱纹,目光敏锐、明亮有神,不像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
当时为了保持采访的统一性,我们设计了一块巨大的背景布,但由于钱老不能离开轮椅,白色的椅背特别显眼,我用我的深色外衣套在了椅背上。
我上去跟他寒暄几句,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基本上听不见。由于听力障碍的原因,老人的声音特别洪亮,周围所有的人都称他为“钱老”,尤其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儿子钱永刚,不叫他爸爸,也称他为“钱老”。钱永刚告诉我,采访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问题也不必问太多,昨天晚上他父亲都做了准备,简短开场后,采访就开始了。
果然,采访开始后,钱老基本上不理会我的提问,自顾自地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但是他说的内容,不仅是我提纲上所提出的,而且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天,钱老情绪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面带孩童般纯真的微笑,他虽因耳背,音调较高,但语速平缓,一字一顿,而且内容风趣幽默,不像是讲一些严肃的、严谨的科学问题,这是的钱学森,似乎不仅是科学家,更像一个大师级艺术家。采访中他大部分时间面带微笑,即使说到在人代会上,因有人质疑“两弹一星”,他说他非常生气,据理力驳时,脸上依然面带微笑。
当他说到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称周恩来遗孀、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老师时(钱老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小学,当时邓是学校老师),和在研究“东风二号”导弹失败原因时,一个女工程师因为着急把脸搞歪的故事时,他都孩童般的笑出了声。但是当他讲到“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让他保重身体时,他脸色凝重了起来,声音哽咽,眼角有了泪光,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动了感情。
原定的半小时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钱老讲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由于钱老说的内容很多,在后来《周恩来》成片时,他的访谈仅用了不到五分钟。其后我们在采访夫人蒋英时,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当时我对钱学森了解尚浅,我印象里的钱学森和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老人没有太多差别,性情平和,衣着简朴,家居陈旧,很难把我所见到的一切和一个神秘的大科学家联系到一起。我更不会想到,十年后在我拍摄《钱学森》传记片时,这将是钱学森一生中唯一一次完整采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分钟画面都极其珍贵。
二、钱学森是新中国的战略科学家
当我加入《钱学森》摄制组时,该片已筹备几年,但一直进展缓慢。我在了解很多情况后,也突然发现,这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工作。首先,由于钱学森长期从事高度机密的国防科研工作,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因此,有关他的影像资料极为缺乏。在“文革”前的所有影像资料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其次,在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几乎不参加具体的科研攻关工作,很难寻找到科研攻关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再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钱学森对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科技发展究竟做了什么贡献呢?在将近几年的采访拍摄中,我们渐渐地对钱学森的科学地位和突出贡献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面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钱学森以一己之力确立了新中国国防科研的战略。
1955年10月,刚过国庆节,钱学森回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将虚位以待几年的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位置授予了他,钱学森也开始了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为力学所做了布局。但第二年,1956年5月,国家召开了全国长期科学规划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副总理组织了六百多位科学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二年规划”。
当时百废待兴,国力又有限,所以要确定几项优先发展的项目。在前期规划项目中,飞机制造名列其中。这是因为,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由于空中打击力量不够,吃了大亏。中央高层痛下决心,一定要打造自己的航空工业,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是力推者之一。但人们没有想到,在规划制定时,航空专业出身的钱学森却态度鲜明的反对优先安排发展飞机。他提出优先发展火箭武器,后来他自己将其转译成“导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刘亚楼曾经说,钱学森的观点让他觉得极为新鲜,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导弹,所以一开始对钱学森的观点不甚赞同。为了说服这些战场的骁将,钱学森专门为他们讲了一课,他用浅显的语言做了完美的说明。他告诉他们,与飞机相比,火箭武器的速度更快,火箭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打火箭,追都追不上。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攻克飞机比攻克火箭技术更难。因为火箭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机械、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研制飞机需要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而研制导弹只需要不到十年。
也许是因为钱学森的学术威望,最终“十二年规划”中,喷气和火箭技术被确定为六项紧急重点任务之一。其中,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设计是由钱学森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合作完成的。
最终,中国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已经能自行设计制造射程达一千公里的中程导弹。而中国的飞机工业的发展却一直面临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安全性。据有关回忆录记载,1964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元帅看到大量的飞机制造出来之后,由于技术和质量问题不能飞行,大发雷霆。从今天看,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了精确打击阶段,导弹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攻击武器。由于钱学森的坚持,中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和生产,使中国拥有了最先进的国防尖端技术;更为可喜的是,由于导弹火箭的研制,带动了中国的航天工程,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相继完成了人造卫星、地球同步卫星、返回式卫星、探月卫星和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依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了显著的进步,但直至今天依然没有制造大型飞机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曾经研制的“运10”也因质量问题而停飞。
五十多年前,如果不是钱学森力挽狂澜,优先发展导弹武器,今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落后世界几十年,这就是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卓越贡献。
二是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统领了中国科研发展。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也是一位教授,专注于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多次强调,希望我们能够把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尤其是晚年的科学思考作为本片的重点。因为他父亲曾告诉他说,他晚年的科学思想才是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思想是无形的,思想的表述总也显得枯燥。钱学森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为我等之辈难以企及。在我们的《钱学森》一片中,我们更多的突出了钱学森的人生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以及具体的科研经历,并未将钱学森的科学思想作为重点。但这并不等于钱学森的思想不重要,只是由于我们今日的认识,尚为肤浅,不足以进行完美表述,说不好还不如不说。
但无论如何,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对中国科学研究领域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尤其因为钱学森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他作为高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所造成的影响之大,也是不可估量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系统”的概念。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学森遭受美国当局软禁之时,他潜心著作,写就《工程控制论》一书,书成之后,他将之赠与恩师冯·卡门,冯·卡门老先生对学生钱学森说:“你的科学成就已经超过了我”。我想,这时冯·卡门所指的并不只是航空工程、喷气动力等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是钱学森提出系统工程的思想,体现出的对科学研究的全新认识与理解,并将给未来科技发展带来革命性意义,冯·卡门无疑是最早认识到钱学森思想价值的人之一。
钱学森回国后,曾有一次未向外界披露的出访:苏联科学院邀请他赴苏进行学术交流。据当时留苏学生宋健(后任国务委员)回忆,苏联科学界对《工程控制论》极为追捧,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1980年《论系统工程》出版,钱学森完成了它的系统理论,在这中间,钱学森不仅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也以他领导的中国高科技事业发展的历程,不断丰富了这个理论,而这个系统工程理论指导并实现了中国高科技研究在极短时间内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能提出一个伟大的科学思想,并以之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程,也只有钱学森一人。
至今,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仍然是中国科技事业创新理论的圭臬。
三、钱学森的遗憾
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除了远超常人的天资以外,也有许多的幸运。他幼年时家道殷实,父亲是教育家,又在教育部供职,所以为他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小学和中学,他就读的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也非泛泛之辈。比如他所就读的中学校长林励儒,解放后担任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已负笈美国,躲避惨烈的战乱,在大洋彼岸的和平环境中安心就学。他在美国的老师冯·卡门是著名科学家,在他的帮助提携下,钱学森出成绩、出名都早。回国后,由于他从事的国防科技研究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所关注,因此他也是极少受到各种运动冲击的科学家之一。钱学森一生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考虑以上所说的因素。这么多幸运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也极为罕见。
但是,人生如白驹过隙,生命苦短。钱学森享年近百,已相当长寿,他的人生,他的科学理想,也必定有许多遗憾,有许多未竟之志。
据很多人回忆,每当人们在欢庆导弹研制的成功和卫星上天时,钱学森却从来没有喜形于色。
钱学森在24岁时曾发表一篇题为《火箭》的文章,放出了“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的豪言。那是在抗战前夜的中国,他的理想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后来钱学森成为中国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的主导者,但他最终只是一位奠基者,他并没有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圆满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在常人看来,钱学森成就斐然,而他自己却心有不甘。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酒泉卫星基地(当时叫做东风基地)举行了庆功大会,在会上钱学森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口就说,我愧对大家!因为“文革”的干扰,中国是晚于日本,成为了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1964年,钱学森曾亲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的完成推迟了八年多。而且他1966年已经提出了中国的航天计划,也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搁浅。对于航天事业的落后,钱学森比任何人都着急。当时前苏联继加加林上天以后,已经完成了“联盟号”载人飞船的太空对接;美国也在1969年首次实现人类登月,完成登月的“阿波罗”载人飞船重达四十六吨,而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只有一百七十三公斤。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领导者是韦纳·冯·布劳恩,美国的许多航天成就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钱学森作为美国军方考察团的一员,赴德国审讯了德国火箭武器的专家,是否审讯了韦纳·冯·布劳恩并没有记载。当时,德国已秘密进行火箭武器研制多年,并拥有六千多枚“V—2”火箭,“V—2”火箭就是在冯·布劳恩的带领下研制成功的。冯·布劳恩是德国科学家,比钱学森小一岁。二战结束后,冯·布劳恩到了美国,成为美国航天科研的领军人物,他最终领导他的团队完成了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计划。
冯·布劳恩所在的美国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科技支持,而钱学森面对的是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一个新生的共和国,钱学森取得成就的难度远大于冯·布劳恩。但是,落后的工业基础和并不强大的科研力量,困扰了钱学森的前进步伐,这也是钱学森的无奈。一个科学家理想的最终实现绝不仅仅依赖他自己那颗超越常人的头颅,更多的需要依赖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文明发达程度。因此,钱学森的遗憾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1977年,冯·布劳恩因患肠癌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5岁。在钱学森生命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所培育的理想之花,最终结出了果实。2003年,中国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遨游太空;2008年,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实现太空行走,中国的嫦娥探月飞船也实现了月球撞击,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四、“钱学森之问”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中国科技腾飞,究竟依靠什么?
钱学森晚年更关注的是人才战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他晚年一直揪心的一件事,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据钱学森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看望钱学森,钱学森对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从那以后,温总理每年要看望钱学森一次,共有五次。每次温总理看望钱学森时,老先生都要提出这个问题。据说,温总理曾将己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请到北京,让他们提出办法来解决“钱学森之问”,校长们提出的办法让温总理深感失望。
钱学森心目中的好学校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考察钱学森的成长之路。钱学森就中学时读于著名的北师大附中,他曾回忆,“当时这个学校的教学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当时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学生,在他准备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各科的老师都给钱学森提出了建议,艺术老师认为他应该学习艺术;国文老师觉得他应该成为作家;而老师希望他能够报考数学系,成为数学家,可见钱学森各科的成绩都不错。钱学森的父亲最终为他选择了机械工程,而钱学森在报考清华留美时,自己选择的是航空专业。
从小时候起,钱学森就酷爱音乐。据他大学里的密友罗沛霖院士介绍,钱学森有很高的音乐天分,大学时他是学校铜管乐队的乐手,同学聚会他总要表演一番,拿到了奖学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街上买外国唱片。初到美国学习时,他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又曾担任MIT最年轻的教授,但他直言并不喜欢这所学校,他更喜欢加州理工学院(CIT),钱学森最终转到加州的加州理工学院,中国有许多科学家都是从这个学院毕业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宗旨是:为教育事业、政府及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加州的学生大都多才多艺,他们的个性发展不受限制,思想也极为自由。钱学森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在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记中说,由于钱学森来自中国,不适应麻省理工学院注重动手实验,他曾向系主任汉·萨克表达不满,这位系主任回答非常简单:“听着,你不喜欢这里,就回中国去算了”。当然钱学森最后还是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在加州理工学院就不一样,他的个性得到了容忍,并且为恩师冯·卡门所喜爱,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教育他的学生就是“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做唯唯诺诺之辈。”在加州的阳光下,钱学森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自己的音乐,也因为音乐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加州校园中的很多学生都体现出了叛逆的倾向,像他的好友J·马林纳,他创设了“喷气实验俱乐部”,也就是著名的“自杀俱乐部”,马林纳就很喜欢音乐,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同学中很多人还喜爱文学,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学生,后来都成就大业。
加州理工学院规模很小,但它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数却在美国的大学中名列前茅,这种鼓励个性自由,培养创造力的校风,让钱学森受用终身。钱学森一直希望中国能有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学校出现,甚至说,他希望有更多的学校像加州理工学院一样。
有“钱学森之问”,或许这样的学校将来会在中国出现。
钱学森是大师,也是一位特殊的人才。特殊的人才需要有特殊的环境来造就。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锻造出一批真正的大师,如今繁荣富强已近在眼前,痛苦艰难正在远去,人们正在呼唤新的大师的诞生,这个日子还会很遥远吗?
(陈真 作者为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总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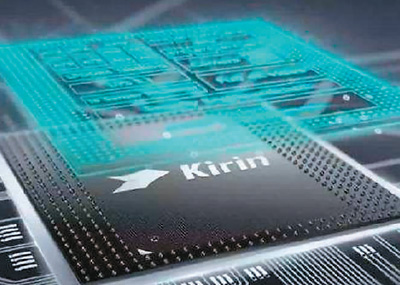

 001
001
 002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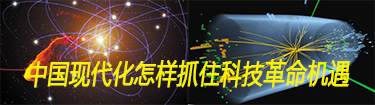 003
003
 004
004
 推荐席位
推荐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