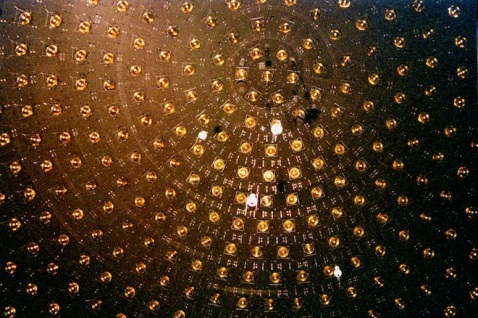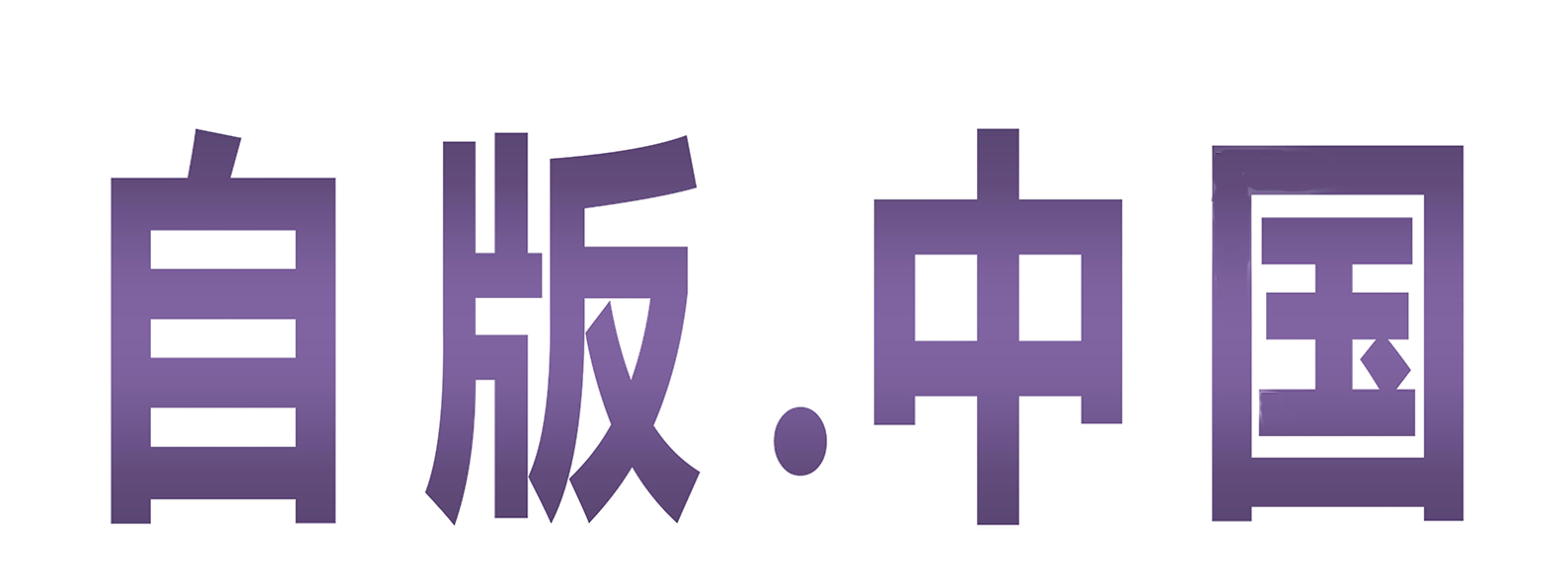碗
作者:孙君飞
2016年12月17日 来源:人民日报
我们的村庄,如一只大碗倒扣在岗上。
在每户人家的榆木、橡木、松木、柏木橱柜里,也倒扣着一只只碗。最大口的碗,需要用两只手恭恭敬敬地捧起来,最小口的碗,连刚学会吃饭的孩子也能够稳稳当当地拿捏在自己的手心里。
富有的人家,他们打开橱柜,我曾经看到琳琅满目的大碗小碗摆满了整整一层甚至更多层。那些瓷碗洁白如雪,质地细腻,散发着柔和的亮光,在釉下彩绘着清新如洗的婆婆纳、蔷薇和兰草。那些包着浆的铜碗,主人的手将碗口摩挲得锃亮。更让我惊奇的是有一次,我还看到一对倒扣着的银碗,凸起的花纹,雕刻的也许是优美卷曲的葡萄藤,也许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某种喜欢卷曲着生长的花草……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端着银碗喝汤吃饭,只在故事里听闻过。故事里还讲银碗甚至能够验毒,这又是怎样陌生、曲折的体验?这只银碗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在家里,母亲做好饭,我像往常那样,帮她从榆木橱柜的暗格里拿出属于我们的粗瓷碗、盘子,以及父亲的黑釉黄陶酒碟。它们散发着沉默的亚光,或者闪出直率的光斑,我明显感到它们的粗糙和寻常。盛在粗瓷碗里的家常小米粥很快烫到我的手指,然而我的内心仍然很安静,仍然像往常那样把第一碗饭小心翼翼地端到父亲的面前。
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从日出后端上一只粗瓷碗开始,到日落后放下一只粗瓷碗结束。太阳是所有人的大时钟,饭碗是我家的小时钟。
父母也见识过别人家的银碗吧,再往前追溯,在爷爷奶奶跟他们分家后,他们去集市购买新家的必需品时,也向往过那种细瓷白碗、精致的釉下彩器皿吧。可是他们只能带回这种粗瓷碗、粗瓷盘子,因为便宜,因为简陋的房屋内只放一只银碗、几只细瓷碗,而没有其它精美物品同它们交相辉映,它们也会黯然失色。
我们的生活称得上穷苦,碗内常常盛着粗粮,盘内常常放着青菜。但是这种生活也很结实牢靠,犹如日益粗壮的树木用根须紧紧地抓住了下面的泥土,大家都抱成团,共同抗击着风雨。
每一天晚上,庄稼地里的农活都完成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下来,踏踏实实地端起饭碗吃饭,偶尔谈起一个计划,严肃的父亲也会纠正一下哪个孩子端碗的姿势不对——这时候我并不在乎自己端的是什么碗,也不在乎能不能顿顿吃到肉。仅仅在别人家里见到过一次银碗,这改变不了我们已经拥有的生活,也改变不了我坐在父母的对面默默吃饭、需要说话时便认真应答的踏实和安宁。谁会在这时候羡慕别人家的银碗呢?父亲和母亲也从来没有用别人家的银碗来激励自家的孩子。
一个热爱劳动,对生活永远抱有希望的人,又坚持端着属于自己的饭碗吃饭,这就是他的尊贵和坚强。我从堪称庄稼好手的父亲身上懂得这一点,我从含辛茹苦的母亲身上也学到这一点。
饭碗在父母手上端得正,端得牢,他们端着粗瓷大碗到村子中央,跟左邻右舍一起边聊边吃,也从容坦荡,毫不卑微。父亲吃罢一碗,母亲回家再给他盛一碗,连我也佩服他的好饭量。有时候邻舍们相谈甚欢,距离人群最近的人家,会为父亲到自家大口锅内盛来一碗米饭,冒着尖儿。父亲以笑致谢,接过来继续边吃边聊,仿佛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
雕刻着卷曲纹的银碗还会在我的眼前闪现,好似在提醒我别忘记它。我一直未曾渴望拥有这样一只银碗。听说有的人家还珍藏着更精美更贵重的玉碗,在夜晚会发出莹莹的蓝光,我的梦想也没有被它激起多少涟漪。我并非不喜爱银碗玉碗,它们在我的心目中是美的创造,我仍会为它们的工艺和传说激动,谁不愿改变自己的家园和生活呢?但我从父母那里知道,整体的更新比局部的点缀更值得追求,人的充沛比物的替换更重要。我们可以倾尽所有买回一只银碗,但是银碗里却空空荡荡,这又有什么意义?
父亲说,即使我们穷得只能变卖家里的梁木砖瓦,也要让你们上好学、读完书,我们在你们身上投光所有的钱,也不担心亏本,成为债户。他们渴望改变的不是简陋的房屋,而是正在成长的孩子。
后来,家里的孩子们陆续从学校里走出来,自力更生,建立小家。大家一起在老家原来的地方盖起新的宽敞的房子,橱柜里的碗也摆放整齐,有细瓷白碗,有来自瓷都的釉下彩名碗,有木碗、塑料碗、不锈钢碗,有单层散热快的碗、双层保温的碗,还有微波炉碗,大大小小,应有尽有。
可仍旧没有用来喝汤的银碗、用来传家的玉碗,现在的生活仍旧不需要它们来体现意义、增添光彩。虽然需要拿出的碗比以往更多,在每年春节,却仍旧能够一个不少地围坐下来,热热闹闹地吃顿饭,这时候更不需要谈论银碗与玉碗了。碗前面的每一个字都不重要,碗后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故事都价值连城,而且令人安宁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