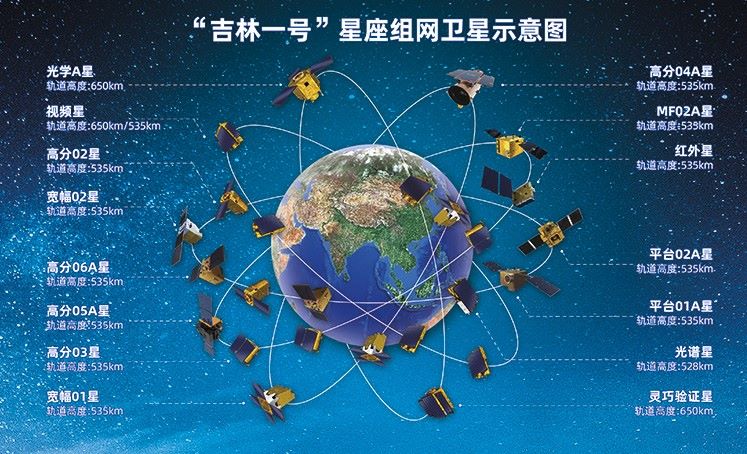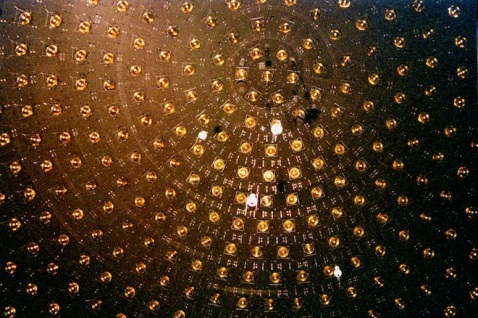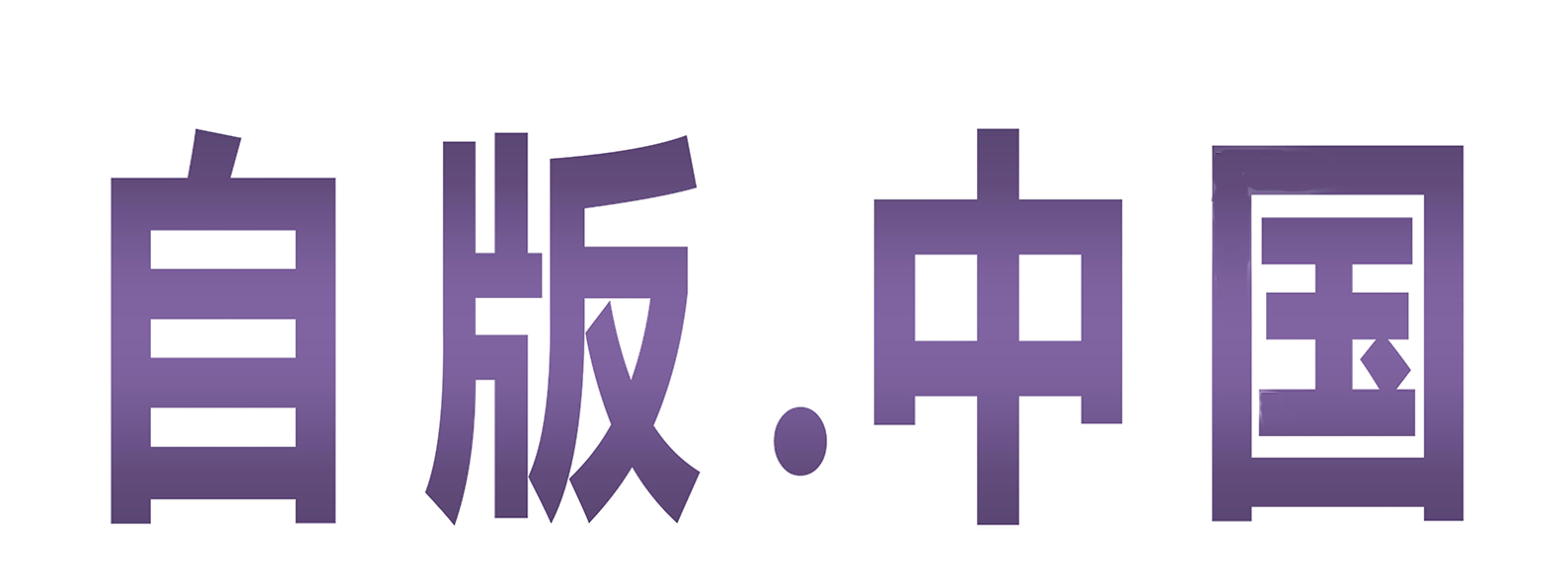21世纪抗癌战略的重大转变
作者:汤钊猷
时间:2011年08月16日 来源:文汇报
笔者从血管外科改行搞癌症临床研究至今40余年,经验不多,教训不少,也遇到一些正反案例,引起笔者的思考。现在到了耄耋之年,有感于“必然”常寓于“偶然”中,有一些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偶然”事例,虽然没有太多文献依据,但说不定深含着有临床和理论价值的东西。
近百年的抗癌战,主要目标是“消灭”肿瘤,应该说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攻克癌症还有很大的距离。早诊早治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疗效,但要再进一步提高就十分困难。看来光靠“消灭”不够,还要考虑“改造”。
一个世纪的努力,“斩尽杀绝”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整整一个多世纪,人们认为癌症是局部病变,是区域性病变。一旦病理学证实为癌,就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等)去消灭它。
外科是治疗实体瘤最有效的办法。癌症手术的范围经历了局部切除、区域性根治和扩大超根治术的过程,以为只要将肿瘤累及的器官和区域性淋巴结一起切除就可达到根治目的。诚然,这些努力使20世纪在实体瘤治疗上取得第一个实质性进展。
20世纪初,放射治疗开始应用于临床,成为癌症的第二大疗法。20世纪中叶,出现了癌症的第三大疗法——化学治疗。之后又加上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以及介入疗法、局部治疗甚至器官移植等,使人类与癌症的斗争取得有史以来最重大的进展。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以“消灭肿瘤”为目标的治疗手段,要想把癌细胞“斩尽杀绝”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可能使问题更复杂。
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从事癌症临床的早期阶段,确实将一切希望放在消灭肿瘤上。例如扩大手术范围,用大剂量化疗,用加大剂量的清热解毒中药,等等,但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后来科学证明,化疗后癌细胞能产生耐药;我们最近的实验研究发现,化疗(奥沙利铂)甚至可增强残癌的恶性程度(侵袭和转移的能力)。当前的分子靶向治疗剂,是分子水平的“魔弹”,但也同样导致未被消灭的残癌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增强。《自然》等一些高层次的杂志,近年陆续刊登了一些文章,指出目前主要的分子靶向治疗剂、抗血管生成剂,虽能抑制肿瘤生长,但却促进癌转移。
2009年,《自然》登载了Gatenby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抗癌战略的改变”,文中指出:“与其消灭肿瘤,不如控制肿瘤;消灭肿瘤促进其抵抗和复发。”这篇文章提示我们,是否应该对过去抗癌战略作一些反思呢?
就肝癌而言,在过去几十年中,因为不知道残癌躲在哪里,无法用局部治疗的办法,只能用全身治疗的办法,我们曾经在手术后用全身化疗去消灭残癌,但无济于事。现在我国大肠癌发病明显上升,因大肠癌切除后发生肝转移的越来越多见。笔者大查房时,每遇到患大肠癌肝转移的病人,都常规问病人“大肠癌手术后有没有用化疗”,几乎每位病人的回答都是说“我手术后每月用一次化疗,已用满6个疗程”,但停药后几个月肝转移便出现,说明全身化疗对消灭大肠癌术后残癌细胞也不是很有用。
笔者想,这好比瓷器店打老鼠,如果老鼠很多,丢一个手榴弹进去,绝大多数老鼠肯定都死掉,瓷器损失当然也不小;但如果只有几个老鼠,那就不值得这样做。因此,要另谋良策。
20世纪的综合治疗基本上是“消灭肿瘤+消灭肿瘤”的模式,展望21世纪,“调整机体”和“调变残癌”,很可能是攻克癌症必不可少的关键途径。
消灭残癌要“恩威并施”,要研究“消灭”以外的办法
1975年和1995年,有两例情况十分类似的病例,即小肝癌切除后4次复发,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前者经配合手术的化疗等各种积极治疗,仍在第一次手术后的第7年死于癌的转移复发;而后者在4次手术之后,因术中输血感染丙型肝炎,必须使用干扰素α进行治疗。奇怪的是,自从用了干扰素α后,肝癌就没有再复发,直到16年后病人仍无瘤生存。值得一提的是,病人用干扰素α始终没有停过。
两位患者一死一生,有没有偶然与必然的联系?我们说必然寓于偶然之中,那么后一位病人能够生存十几年有没有必然性呢?
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的一位博士生在研究用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肝癌术后转移复发时,发现干扰素α如果用的剂量较大,时间较长,确实可以减少患肝癌裸鼠肝癌切除后的转移,并延长裸鼠的生存期。这个结果2000年在肝脏病的顶级杂志《肝脏病学》发表。但干扰素α也不是对所有癌症病人都有预防转移复发的作用。不久前我们发现小核糖核酸26这个分子表达低的肝癌病人,使用干扰素α的效果较好,而表达高的效果差,说明事物是复杂的。
21世纪的抗癌战争除继续寻找新的消灭肿瘤的办法外,将重点研究“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的办法。过去一个多世纪,正因为抗癌战是建立在病理学的基础上,因此科学家都集中注意力去研究如何消灭肿瘤一方,导致只“看肿瘤”,而忽视“看病人”,从而没有足够重视改造机体一方,忽视了机体强大的抗癌能力。
我国的中医中药很早就有“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笔者75岁时启动了一个课题,从荷人肝癌裸鼠的实验研究中证实,含5味中药的“松友饮”可诱导癌细胞凋亡,延长动物生存期;并发现它的一些分子机制,如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上调E钙黏蛋白,从而降低了肝癌细胞的恶性程度。由此笔者深信,在抗癌战争中,中医学是值得探索的。
笔者1968年由血管外科改行搞肝癌研究,当时住院的都是晚期肝癌病人,除极少数能手术外,治疗手段只有化疗和中药。出于救治病人的迫切心情,不能开刀的也勉强开,化疗小剂量不行就用大剂量,以为再加上中药会更好。当时没有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所谓“抗癌中药”以为剂量越大越好。在大剂量化疗的同时还要加上攻下的中药,以为西医化疗攻癌加上中医攻癌会更好。其结果每天都有病人出血,诉口干,汗出,无食欲,且很快死亡。
上面的情况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其根源是将中医中药当成西药来应用,是“废医存药”的结果。后来粗粗学了一点中医理论,认识到中医治病重在恢复失衡,而不完全是通过中药去消灭肿瘤,所以用药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用量越大越好。认识到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需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治疗。癌症病人既有癌需要“攻”,也有病人机体需要“补”。于是采取攻补兼施的办法,即在攻癌的同时,加上一点扶正的中药,病房情况便有所好转,病人出血率下降,生存也长一些。
由于我们是西医,化疗总是要用的。后来发现中西医结合还有新的攻与补的问题。实际上化疗属于很强的攻下之品,最后我们从实践观察到,当西医用化疗时,中医只能补,而不能攻补兼施,更不宜同时用攻下的中药。上海肿瘤医院于尔辛教授在肝癌病人用放射治疗的同时,也发现合并健脾理气中药效果比合并使用清热解毒和(或)活血化瘀之品要好。
最近笔者注意到,一些传统“非抗癌药”居然还有抗癌作用。除阿司匹林被证实长期服用可降低多种癌症风险外,《癌症研究》2009年报道,治疗结核病的利福平,是可以口服的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可用于肝癌治疗;《癌细胞》杂志2010年报道,常用的抗真菌药依曲康唑,也可干扰某些信号通路而抑制肿瘤生长;用于骨质疏松的药物,居然还可以作为多发性骨髓瘤的一线治疗(《柳叶刀》,2010);治疗糖尿病药噻唑烷二酮类,慢性给药也证实有抗癌作用,其作用主要是抗增殖,对肝癌也有用(《肝脏病学》,2010)。这样看来,抗癌之路还是很宽广的。
如果癌不转移,就变成良性肿瘤。为此,研究癌转移是攻克癌症更本质的方面,也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
以前癌症诊断主要回答“是与否”,而21世纪还要回答某一病人所患癌症的“善与恶”。所谓“善”,指恶性程度较低,不容易出现转移复发;所谓“恶”,指恶性程度较高,容易出现转移复发。目前,我们发现一种称为“骨桥蛋白”的分子,无论术前或术后,都有一定预测转移复发的价值。相关文献也认为,骨桥蛋白表达可预测肝癌肝移植的预后。这类指标之所以重要,就是可以作为治疗选择的参考,可以作为估计预后并采取对策的参考。预期21世纪,将有一些准确性较高的指标成为临床的常规。
过去认为,癌转移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厉害,现在的研究证明,转移能力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可双向改变。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于癌转移,百年前就已经提出“种子与土壤”假说,但过去比较强调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而近年则发现土壤也可影响种子的特性。我们在建立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过程中,观察到改变“土壤”可以育出相仿遗传背景但不同转移潜能和转移靶向的细胞,例如,肝癌细胞放在肺提取物中去培育,它就更容易转移到肺,如在淋巴结培育,就变成容易转移到淋巴结。这提示微环境(土壤)在癌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癌转移研究不能只针对癌细胞,如何改造土壤将是大有可为的。
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能阻断其中某一个环节,癌细胞的转移也可能就会夭折。为了研究干预治疗,我们建成在肝内、肺和淋巴结转移率极高的人肝癌裸鼠模型。还建成接种在裸鼠肝脏出现肺转移的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有了这些模型,就可以用它来试验各种“干预”的措施,包括改变肝癌细胞遗传特性的措施;对血管丰富的癌症,通过干预其血管生成,也是一条途径。临床常用的干扰素,就有预防肝癌切除后转移复发的作用,它的作用也和抑制血管生成有关,这些都给21世纪的癌症临床带来新的希望。
作者简介
1930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教授,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
肝癌早诊早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最早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获1979年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从事肝癌转移研究,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2006年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版文字整理自汤钊猷院士新著:《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上海科技出版社2011年8月版。
相关链接 重新认识癌转移
由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近年在“癌转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对病人、家属、医生和研究人员来说,都有参考价值。
癌症,包括癌转移是全身性疾病
它是外部环境与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体内则是宿主、癌和癌的微环境三者互动的结果。其中宿主应该包括病人的遗传背景,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状态。换句话说,癌转移是一个受到内外因素影响的不断变动的过程。因此,病人的情绪、饮食、活动以及各种治疗等,也同样可以影响癌转移的潜能。
癌转移潜能源于原发瘤
过去认为癌转移是癌的晚期现象,是癌在进展过程中“克隆筛选”的结果,就是随着癌的发展,能转移的癌细胞比例越来越多。但我们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研究发现,早期小的癌症也可以有很高的转移潜能。这个发现,丰富、补充了经典的癌转移理论。笔者以为,癌转移潜能的获得主要来自原发瘤,但在其进展过程中受内外因素包括微环境等的影响而可逐渐增强。为此,转移防治应重视抓源头、抓整体。
癌转移相关的分子不仅可以从癌细胞中去寻找,还可以从癌所处的微环境(包括血管内皮细胞)去寻找
过去我们找和癌侵袭转移有关的分子(基因和蛋白),只盯住癌细胞去找,找那些与癌侵袭转移有关的分子。后来和美国同行合作,发现癌周围的正常肝组织中有17个基因也可以预测病人的复发转移倾向。重要的是,这17个基因不是直接和侵袭转移有关的,而是和免疫、炎症有关。换句话说,不仅是与癌细胞的侵袭转移有关的分子和癌转移有关,而且癌周围的免疫炎症微环境也和癌转移有关。特别是免疫微环境是受到全身免疫系统调控的。已有证据表明,很小的癌症已可在血液中找到癌细胞,即循环中的癌细胞。
癌转移潜能是可变的——可变坏,也可变好
过去认为癌转移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厉害,现在的研究证明,转移能力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可双向改变。例如,肝癌细胞放在肺提取物中去培育,它就更容易转移到肺,如在淋巴结培育,就变成容易转移到淋巴结。
我们设计了一个含5味中药的小复方“松友饮”,它可以减少两个和肝癌转移有关的分子——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使癌细胞恶性程度减轻;在动物实验也看到它可使带瘤动物的生存期延长。
2010年的《科学》杂志有一篇陈竺教授的文章,发现砒霜(三氧化二砷,砷剂,一种传统的中药)所以能治疗一种类型的白血病,就是因为它可以和引起该白血病的蛋白结合,使白血病细胞的分化程度变好一些,这样恶性程度就低一些,从而达到部分“改邪归正”的目的。一篇评论说,这可能提示砷剂治疗其他癌症的潜在价值。
抗炎治疗有助抑制癌转移
过去认为发炎和癌症完全是两码事,但近年研究发现,很多癌症发生在感染、慢性刺激和炎症的部位。在癌症微环境中,有许多炎症细胞,这些炎症细胞使癌细胞得以生存、增殖和迁移。这为抗癌转移治疗增加了新的思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对癌症有潜在防治作用的抗炎药物,如阿司匹林等,在癌转移治疗上也可能有用。将来,如果医生对癌症病人开一些抗炎药物,大家就不要大惊小怪了。